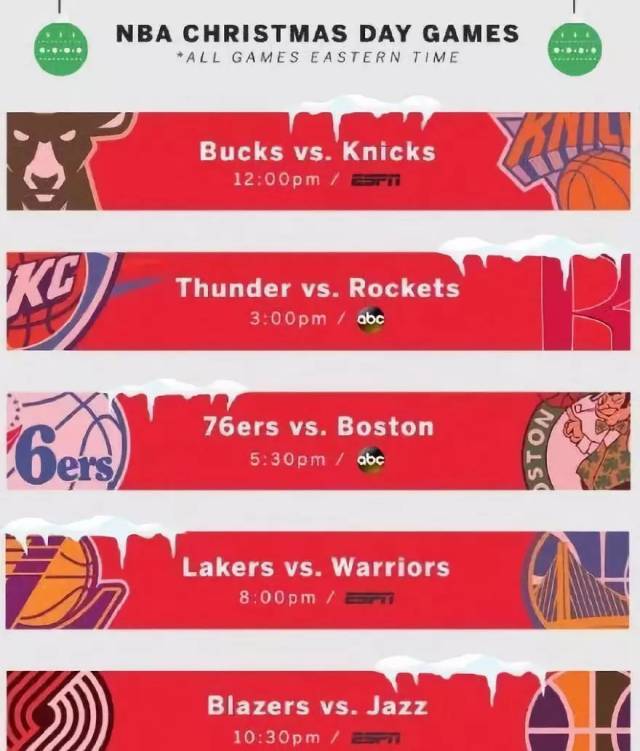程民生:论“耕读文化”在宋代的确立
作者:程民生
来源: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20年第6期

《清明上河图》卷,北宋,张择端作(故宫博物院藏)
我国古代始终是农耕时代,所孕育的自然是农业文明。这就决定中国文化有着浓重的农业、农村、农民色彩,中国农业有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,或言农村、农民中诞生出大多数知识分子。这一特征的精髓概念,就是耕读文化。耕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,影响极为深远。那么,像所有文化都有一个生长过程一样,耕读文化具体是何时、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确立的呢?对此,学界不乏说法,然似缺乏论证,更未必正确。有学者关注到宋代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,并有精彩论述,但多是从文学、建筑等角度的认识,从历史学角度而言,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论证研究与揭示。
一、“耕读文化”的渊源及在宋代的确立
一般而言,耕读一体的形态先秦即存在,区别是形式不同、程度不同、普及范围不同。如果从士大夫角度而言,读书人无论从哪里入仕,家中大多总是有田产的,但不一定直接耕作或经营。科举制实行后,农家子弟入仕前以及致仕后,也还会与耕作经营打交道,但也未必直接耕作。耕读概念包含两层意思,一指读书者和耕作者是同一人物,即躬耕躬读、半耕半读,是为个人的耕读;二指一个家庭同时经营农业和学习读书,其成员一部分主要耕以生存,一部分主要读以发展,读书者通常都是子弟,是为家庭的耕读。
耕读分合作为一个问题的提起,应当从孔夫子说起。自从春秋时期民间教育兴起,孔子就力主区分耕读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樊迟请学稼。子曰:‘吾不如老农。’请学为圃。曰:‘吾不如老圃。’樊迟出,子曰:‘小人哉,樊须也。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。焉用稼。”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又进一步指出:“君子谋道不谋食,耕也,馁在其中矣;学也,禄在其中矣。”反复强调的是,读书做官是君子的职业,耕田种地则是小人的职业,不可混合在一起,亦耕亦读,正如君子、小人不会融为一体。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教育家,他的意思大概还有既然读书,就应专心致志,不能一心二用;况且农耕跟着长辈就学会了,而他教的是道理。其学说的继承发扬者孟子,同样秉承读书做官的理念,并有所发挥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:“然则天下独可耕且为与?有大人之事,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,而百工之所为备,如必自为而后用之,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,或劳心,或劳力;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;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。天下之通义也。”强调阶级差异,宣扬的是要做官以俸禄养家,而不能屈尊耕田,劳心者与劳力者有着天经地义的差别。孔孟圣言,遂使士农对立,也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,并随着儒家地位定于一尊,成为统治思想,后代以至于形成了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不良风气,把读书事业抬到远离农业的高空。
然而,即便有此圣贤教导,毕竟是“重农”的农耕社会,毕竟文化要发展,有此两大客观基础,耕读不可能断然分开。实际上,耕而读、读而耕的情况一直陆陆续续、星星点点的存在。班固曾回顾道:“古之学者耕且养,三年而通一艺,存其大体,玩经文而已。是故用日约少,而蓄德多,三十而五经立也。”这也是“三十而立”的一个内容,之所以持续时间长,是因为半工半读,而非全心全意只读书。孔子时代也遇见过耕地的隐士,即《论语·微子》所载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”。有关隐士耕种的例子很多,属于“士”而后“耕”,耕是隐的形式,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耕读模式。
汉代以来,耕读事例渐多。如兒宽“以郡国选诣博士,受业孔安国。贫无资用,尝为弟子都养。时行赁作,带经而锄,休息辄读诵,其精如此”。一边为人打工耕作挣钱,一边读书,打工耕作是为了读书。常林与其相同:“少单贫。虽贫,自非手力,不取之于人。性好学,汉末为诸生,带经耕锄。”三国诸葛亮自我介绍道:“臣本布衣,躬耕于南阳,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这属于隐耕。另一典型就是晋代陶潜,他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“卧起弄书琴,园菜有余滋”。这是先读书做官、后耕田读书。三国西晋时期学者、医学家、史学家皇甫谧二十余岁时,“就乡人席坦受书,勤力不怠。居贫,躬自稼穑,带经而农,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”。“带经而农”,即边耕边读。唐代的事例,如“儒翁九十余,旧向此山居。生寄一壶酒,死留千卷书。栏摧新竹少,池浅故莲疏。但有子孙在,带经还荷锄”,也是耕读的意思。
从上大致可以看到,宋以前的耕读者成分简单,主要是隐逸之士和学生;数量也有限,尚谈不上普遍;多是以读为主,以耕为辅,或耕只是读的一种辅助形式,二者没有水乳交融,相辅相成,更缺以耕为主的读、从耕出发的读。朱熹指出:“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,耕且养而已矣。其所以不已乎经者,何也?曰,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。学始乎知,惟格物足以致之。知之至则意诚心正,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。若此者,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,而不知其所以然者,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,夫岂用力于外哉?”他指出:古代学者的耕是为了养学,是学的经济基础。其意义主要在于不将耕视之为贱事,并未耕读并列并重,更非底层的由耕而读,仍不是完整的耕读文化,只是初级阶段的一股源流。
二、“耕读”词汇在宋代的出现
流淌千余年的耕读文化上游,到宋代汇聚成洪流。随着唐代中后期士族门阀的瓦解,以及宋代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,在文化方面出现三大新形式。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;二是教育发达,文化普及,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底层民众有学文化的热情和条件;三是大量的士子、落榜考生没有或未能科举入仕,沉淀在农村家乡,以新的面貌继续务农。因而,边耕边读、半耕半读,就成了常态,“耕读”二字联合,作为专词在宋代应运而生。
检索爱如生等有关大型古籍数据库,最早出现“耕读”二字连用的,似是北宋中期的曾巩,他在孔延之墓志铭中写道:“幼孤,自感厉,昼耕读书垄上,夜燃松明继之,学艺大成。乡举进士第一,遂中其科。”这是一个耕读成功例子的亮相。但是,真正将其作为一个词语和概念使用的,是北宋后期官员唐庚,他所拟的考试策论题目就是《耕读》,让考生论述:
“问:先王之时,其所谓师儒者,乃六卿之吏;而其所谓士者,乃六卿之民。故为士者未尝不耕,而为农者未尝不学。《周官》以九职任万民,而士不与焉,盖以士寓其间故也。周道衰,管仲始以新意变三代之法,定四民之居,而士农之判,盖自此始。而孔子、孟子之教,以耕稼为小人之事,非士君子之所当为,而从学之徒一言及此,则深诋而力排之者,何也?舜不耕于历山,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,伊尹不耕于有莘之野乎?何害其为圣且贤。而孔子、孟子之论如此,必自有旨也。有司愿与闻之。”
他提示的耕读演变历史是:三代时,只有六卿之官吏与六卿之百姓两类,读与耕并无分野。春秋时,管仲划分人民为士农工商四民,人们才各司其业。至孔孟,将读与耕强化为君子与小人之事。实际上,古来圣贤无不耕作,孔孟为何这么说呢?这一试题的提出,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:耕读原本就应当为一体,孔孟断然分开的深意何在?其实际意义,未尝不是不便直接批判孔孟的婉转措辞,更是为当时流行的耕读模式扫清理论障碍,寻找历史依据,为“耕读”一词和耕读理念的登台鸣锣开道,大造舆论。
耕读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旉也曾纠结于此,试图破解。他一生隐居躬耕,并撰写《农书》,这就无法回避孔孟的观点。为了使自己的事业符合儒学,他努力向其靠拢,调和耕读对立:“仆之所述,深以孔子不知而作为可戒……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志。”出版时又对官员说:“樊迟请学稼,子曰,吾不如老农。先圣之言,吾志也。樊迟之学,吾事也。是或一道也。”实际上仍然未能调和,既不能洗白孔孟,也不能洗白自己。

《农书》(图源:网络)
至南宋,耕读一词进一步扩展,将耕读名之于室额。李敬子因故被免官,“敬子既归,躬锄耰,其乐不改,治庙祀,裁古今彛制为通行,家事绳绳有法度。筑室曰‘耕读’,以待学者,横经其间,士争趋之,舆议亟称其贤”。自己实践耕读,并号召广大士人耕读,受到士绅的高度赞扬。还有士大夫把耕读标之于堂号。合肥长官、赵鼎曾孙赵纶作示子赵玉汝诗云:“颜筋柳骨徒尔工,岛瘦郊寒竟何益?劝汝耕田勤读书,丰公非是无官职。”其子赵玉汝“今于居之堂,摘末联‘耕读’二字以昭扁,志不忘也”。为了纪念乃父,表明孝心,将父训凝聚为“耕读”二字,揭之为匾额,建堂明志。宋代遗民卫富益,还将这一概念自命为别号。他宋亡不仕,隐居教授著述,有《四书考证》《性理集义》《易经集说》《读书纂要》《耕读怡情》等著作。晚年还故里,“自号‘耕读居士’,绝不言世务,不理城市”,把宋代的耕读理念带到元代,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姿态。
这些情况表明,从“带经而锄”的行为开始,流传了千年之久的耕读事实最终在宋代概括提炼成一个确切的词语,耕读理念形成并进入文化层面,意味着耕读现象的普遍。
三、耕读理念的确立与实践
在文化普及、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,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。依据不同需求和形式,大致可分为两大类。
第一类是士人的耕读生活。其中又分几种形式。
一是“耕隐”。南宋士大夫牟巘在《耕隐说》中,阐述这种耕读隐居的生活时说:“自昔以来,士率以隐遁为高,事或不同,其致一也。有隐于耕者,长沮、桀溺耦而耕是也……吾友俞好问之田邻蔡道明,字子诚,自号‘耕隐’,其慕耕耦隐者欤?‘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’,为此言者可谓知本矣,要使其后人长留得读书种子耳。吾老农也,曾无寸土可以施其鉏镬,于耕隐盖不胜健羡,因书而归之。”这是耕读最早的源头之一,至宋代更加普遍。如宋真宗时陕西隐士刘巽,“治《三传》,年老博学,躬耕不仕”。北宋中期的孔旼隐居汝州龙山之蚩阳城,“性孤洁,喜读书。有田数百亩,赋税常为乡里先”。虽是孔子后裔,更是一个有文化守法令的农民。
二是耕读作为事业和生活方式。如胡宪原本太学生,后“揖诸生归故山,力田卖药,以奉其亲”。绍兴进士范良遂,“笔研不灵,卜筑江上,且耕且读,书与学俱晓。自号墨庄,有诗集刊于家,吴荆溪为序”。南宋学者张邦基,失意后“归耕山间,遇力罢,释耒之垄上,与老农憩谈,非敢示诸好事也。其间是非毁誉,均无容心焉。仆性喜藏书,随所寓,榜曰‘墨庄’”。这些士人将耕读作为良好的归宿。远在广东沿海的南恩州莫家,从南宋末期开始一直践行这一模式:“宋至嘉定间,而天祐公又赐进士及第,称世家矣。载传世而生阿玖公,始迁恩州那西村,以耕读为业,世有隐德。”将耕读作为世代相传的事业。
三是作为奋发图强的起点和形式。更多的情况是士人不得不边耕边读书,寻求出路。正如晁补之所言,这是宋代最为普遍的现象:“补之尝游于齐、楚之郊,见夫带经而耕者,莫非求仕也。”都是农家子弟为了改变命运,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而入仕,是“鲤鱼跳龙门”式的拼搏形式。
第二类最重要,即农民的耕读,这是新的主体或基础。
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,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,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:一是自上而下的,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,读书之余经营农业;二是自下而上的,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、不可能,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。第一层意思在宋代已经毫不值得赞赏,因为早已不是孔夫子时代读书大都能够做官,而是大都不能做官,况且连商人也早就“以末致富以本守之”,农耕是本,是历代的基本国策,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敢轻视。耕读模式最有价值的内涵,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纷纷读书,即自下而上的读书热潮。
宋代还出现一个与耕读一词相关的新词:“识字农”。如陈著:“世多多才翁,谁识识字农。”陆游也云:“颓然静对北窗灯,识字农夫有发僧。”北宋苏轼早有“吏民莫作长官看,我是识字耕田夫”的提法。虽然都是士大夫耕读的自况,但读书识字的农夫也确实众多。宋末元初的黄应蟾云“荛夫被儒衣,耕叟辟家塾”,便是宋代许多农民学文化、有文化的真实写照。例如“田父龙钟雪色髯,送儿来学尚腰镰”。具体例子如北宋洛阳富裕农民王德伦,全家识字:他“常于孟春读诵《金刚经》数千遍……尝读《大戴礼》,觊取青紫于世……购藏经籍,以训子孙为务”。有子四人,一人“翼习《毛诗》,学究志业”,一人“亦常专经,止于中道”,一人进士及第入仕,一人“幼读诗礼”后“废书而置产”。他的妻子也读书识字:“常说孟母择邻之事,以晦诸子,又好看《多心经》。”此可谓典型的耕读之家。北宋后期的毛滂自言其家三代耕读不辍:“某本田舍家,自父祖皆昼耕锄,夜诵书。”常德府富农余翁,家中专有书房,“家岁收谷十万石……庆元元年六月,在书室诵经”。两宋之际的张守指出:“中上之户稍有衣食,即读书应举,或入学校。”在文风浓郁、教育发达地区,相当一部分人家都是如此。如叶適所说:“今吴、越、闽、蜀,家能著书,人知挟册,以辅人主取贵仕。”具体如福建,“闽俗户知书”,连被差点为乡兵的人,也“大抵举子也”。其中的建州,有半数农民家庭已是半耕半读:“山川奇秀,土狭人贫,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。”读书识字只是生活的必需,未必非要参加科举。
把耕读当作人生快乐之事,是耕读文化普及流传的前提之一和内在因素。四川士人家颐就说:“人生至乐无如读书,至要无如教子。”吕午在《李氏长春园记》中指出:“人生天壤间,有屋可居,有田可耕,有园池台榭可以日涉,有贤子孙诵诗读书,可以不坠失家声,此至乐也,而纡朱怀金不与焉。顾能备是乐极鲜……间有高堂大厦,绚丽靓深,西陌东阡,日增月广,园囿景物之可纵所如,兰玉绳艺之相为辉映,岂不可乐?而缓役于富贵利达,如蜗牛升高而不疲,蝜蝂好上而不已,卒于钟鸣漏尽,未尝得一日少安厥居,载美酒、逐清景以自乐其乐者,亦可怜已。”有田可耕,有子孙读书,就是人生难得的乐事,胜过荣华富贵。李日升“平居不易言,不以事不造公寺,喜读书,乐于耕事”。既喜欢读书,又喜欢耕作,就是不喜欢与官府打交道。南宋中期的莆田人方审权,“少抱奇志,从伯父特魁镐仕湖之,所至交其豪隽。及归,慨然罢举。家有善和之书、东冈之陂,汾曲之田。君曰:‘吾读此耕此足了一生矣。’始者人疑其功名顿挫愤悱而然,既而久幽不改,以至大耄,安之如一日……君博古通今,父子皆能诗,有《真窖》《听蛙》二集。其志业不少概见于世者,皆于诗发之”,科举失利后,遂安心耕读终生,那些远大志向则通过诗歌发泄。吴兴人张维,“少年学书,贫不能卒业,去而躬耕以为养。善教其子,至于有成。平居好诗,以吟咏自娱。浮游闾里,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,遇物发兴,率然成章,不事雕琢之巧,采绘之华,而雅意自得。倘徉闲肆,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。盖非无忧于中,无求于世,其言不能若是也”,都是以耕读为快乐人生的事例,意味着耕读生活对士人很有吸引力。这不仅是个人爱好,还成为一方风俗。如抚州“其民乐于耕桑,其俗风流儒雅,乐读书而好文词,人物多盛”,是良性循环的典型地区。
耕读盛况因而形成。如陆游有诗云:“农畴兴耒耜,家塾盛诗书。”具体情况是,冬季农闲,农家开始了另一种繁忙即延师教子:“十月东吴草未枯,村村耕牧可成图。岁收俭薄虽中熟,民得蠲除已小苏。家塾竞延师教子,里门罕见吏征租。老昏不记唐年事,试问元和有此无?”这些都是倡导和描述耕读之风,并认为前代无此习俗。刘克庄说:“闽人务本亦知书,若不耕樵必业儒。”务本知书即耕读的统一,已经十分普遍。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重大的副产品是,新一轮的兼并在这种背景下兴起:“古者士则不稼,大夫不为园夫红女之利,今者公卿大夫兼并连阡陌。”其特点就是士大夫热衷于买地耕种。
宋代虽然还未出现“耕读传家”一词,但这个理念已然形成。具体事例,如苏辙在给诸子的诗中写道:“般柴运水皆行道,挟策读书那废田?兄弟躬耕真尽力,乡邻不惯枉称贤。裕人约已吾家世,到此相承累百年。”这表明其家已有百年的耕读传统。南宋前期舒邦佐的传家训词中,就有“后世子孙,优必闻于诗礼,勤必苦于耕读。教子择姻,慎终追远”。显然就是耕读传家的意思。陆游说得更直接:“力穑输公上,藏书教子孙。”类似例子很多,如黄岩赵十朋有诗云:“四枚豚犬教知书,二顷良田侭有余。鲁酒三杯棋一局,客来浑不问亲疏。”本人是“贤士”,家有两顷农田,四个儿子都读书。王十朋“亦有东皋二顷,两子皆学读书”,作诗云:“薄有田园种斗升,两儿传授读书灯。”陆游晚年在家乡当“识字农”时,有诗云:“大布缝袍稳,干薪起火红。薄才施畎亩,朴学教儿童。羊要高为栈,鸡当细织笼。农家自堪乐,不是傲王公。”“诸孙晩下学,髻脱绕园行。互笑藏钩拙,争言斗草赢。爷严责程课,翁爱哺饴饧。富贵宁期汝?它年且力耕。”从诗中可以看出,其所教后代子孙的人生目标并不是为科举入仕,而是做有文化的农民。一般而言,读书求知目的有三:知识改变命运,知识服务生活,知识提升身心。读书大多不能改变命运,但可以改变生活方式,改善生活质量。如张邦炜先生所言:“宋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是多元的,其中较为常见的大致有以下三种。一是为谋生而读书。二是为做官而读书。三是为救世而读书。”这是宋代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亮点,也是耕读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。
中国古代耕读传家的理念从宋代开始确立与普及,这是宋代民众文化水平高起点的基础。在宋人看来,耕读都是人生的必须,其中耕是生存的需要,读是发展的需要;耕是本分,是物质需要;读是更新,是精神需要。基本生活环境改善之后,宋人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加强烈,也就是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上升,主要还是为了子孙的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、社会地位的提升。如黄震说:“人若不曾读书,虽田连阡陌,家赀巨万,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。”意思是农民应当读书,否则土地再多也只是普通百姓,读书的农民才有品位。文彦博甚至明确指出:“则知富于文者,其富为美;富于财者,其富可鄙。”流传至今的俗话“三代不读书,不如一窝猪”,就是民间对耕读或农民读书的强调。更深入普通农民人心的是卜算文化,北宋邵雍辑录的古代占梦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态度:梦见“耕田读书,大吉。占曰:且耕且读,务本之象。必名利双全,大富大贵也”。此书虽据传为晋代葛洪编撰,实际上此前并无文字等痕迹,也即并未在社会中起作用。只有在宋代适宜的环境中,才能广为流传。
在理论上,历史进程证明孔孟耕读分离的主张不符合社会实际和历史发展,宋代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社会现实,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士农界限。更关键的是,耕读合一理念与习俗的形成,是对孔子耕读分离的公然反叛与不屑,确属宋人大胆解放思想的表现。
耕读文化的关键是读,全国范围内,不读而耕者毕竟是大多数,读而耕者,通常多见于文风昌盛的地方。
四、宋代耕读文化的效应
耕读模式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,意味着二者的相辅相成。宋代历史证明了这些辉煌成就,在此主要提示三个方面。
第一,对知识分子和文化而言,耕作的实践有利于思维的创新和学问、创作题材与水平的提高。例如济州士人邓御夫,“隐居不仕,尝作《农历》一百二十卷,言耕织、刍牧、种莳、括获、养生、备荒之事,较之《齐民要术》尤为详备。济守王子翻尝上其书于朝”,成为由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农学专家。其他如陈翥、邓御夫、陈旉、胡融、陈景沂等在乡间躬耕自食,同时撰写农书以总结生产经验,从而“把私人农学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”。如陈翥写出世界第一部研究泡桐的专著《桐谱》,刘蒙著成第一部菊花专著《菊谱》等即是。有学者统计宋代农书141部,而唐以前历代(含唐)农书总计也不超过80部,足见宋代是传统农学迅猛发展的时代。应该说,这正是耕读文化的产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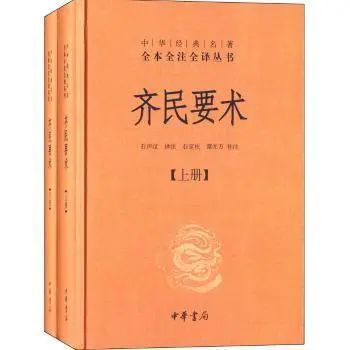
《齐民要术》(图源:网络)
最典型的人物是两宋之际的陈旉。他一生隐居躬耕在淮南的西山,是位饱学之士:“西山陈居士,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,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,贯穿出入,往往成诵,如见其人,如指诸掌。下至术数小道,亦精其能,其尤精者易也。平生读书,不求仕进,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。”针对“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,孔门所不学,多忽焉而不复知,或知焉而不复论,或论焉而不复实”的耕读分离状况,立志隐居耕读,著《农书》三卷:“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之志,固非腾口空言,夸张盗名,如《齐民要术》《四时纂要》迂疏不适用之比也。实有补于来世云尔。”多年的亲自实践,使之发现前代名著《齐民要术》等的“迂疏不适”,敢夸海口。书中有不少突出特点,至今被称为“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”。绍兴年间完成《农书》后,正招抚难民垦辟荒地的知真州洪兴祖如获至宝,“取其书读之三复,曰:‘如居士者,可谓士矣。’因以仪真劝农文附其后,俾属邑刻而传之”。作为首批耕读的农学家,他是耕读文化的杰出代表,在耕读文化确立过程中起到标志性作用。
另一突出事例是农诗事的兴盛。有关研究表明,宋代农事诗的创作异军突起,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几类诗作;宋代是农事诗发展的高峰期,达到其艺术内涵的顶峰。这些成就都是耕读文化的产物,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内容,使之更接地气,更有内涵,也使农业情况更多、更具体地传播与士大夫,使之更加关注。
第二,知识、知识分子大量进入农业生产领域,大大增添了农业的文化含量,促进了农业发展。典型如南宋初期四川人苏云卿隐居在南昌耕作:“披荆畚砾为圃,艺植耘芟,灌溉培壅,皆有法度。虽隆暑极寒,土焦草冻,圃不绝蔬,滋郁畅茂,四时之品无阙者。味视他圃尤胜,又不二价,市鬻者利倍而售速,先期输直。夜织履,坚韧过革舄,人争贸之以馈远。”他开辟荒地种植蔬菜,以渊博的知识功底和聪颖,很快成为种植高手,无论冬夏均有蔬菜上市,而且品质优良,深受市场欢迎,商贩以至于提前付款订货。意味着无论技术还是经营,都是非常先进的。例如冬季蔬菜的商业化种植,是如何营造像现代塑料薄膜大棚那样既温暖又光线充足的环境的呢?耕读结合,提高了生产、经营水平和产品质量,又丰富了文化的实践经验。
第三,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,是促使文化普及到农家。正如北宋朱长文所谓:“虽濒海裔夷之邦,执耒垂髫之子,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,裦然而赴诏者,不知其几万数,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。”所言“执耒垂髫之子”,就是农家儿童。除了一心想通过科举入仕的大众潮流以外,非科举功利的识字读书者颇多。如会稽陈姓老人,生三子,有孙数人,“皆业农……子孙但略使识字,不许读书为士”。宣和末,河北“有村民颇知书,以耕桑为业……其家甚贫”。有的农家送子弟入学校读书,仅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役:“学书意识偏傍,与门户充县官役足矣。”在文风浓郁的东南地区更是普遍,如邵武军“力农重谷,然颇好儒,所至村落,皆聚徒教授”。读书成为农家风俗,也即耕读文化的普及与硕果。
当然,耕读文化的效应绝不止于此,对官员的政治理念、治国行为等也有不小的影响。总之,耕读文化自从宋代确立以来,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当代学者对耕读文化予以高度评价,认为耕读文化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趋向,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寄托”。“对于读书之人来说,耕读生活是他们最基础的生存形态”。同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文化形态确立于宋代:“班固描绘的耕养之道的蓝图被南宋士绅践行了”;“耕读传家是乡土中国生活观念的底色,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的塑造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联……在理学重新塑造后的人生信条中,耕读传家成为致太平事业的起点,读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……它继续演进、发展,最终凝定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生活观念,对后世影响深远”。所言不乏真知灼见,但限于所论主旨,完全是从士大夫角度看问题,没有注意到广大农民起到的决定性作用,也没有看到北宋的盛况。
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遍及农家的对联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,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。所有这些,都是宋文化的历史贡献。
余 论
耕读文化源远流长,由零星的隐士行为发展为广大的士人行为,扩展为普通的农家行为,从特殊现象到普遍的人生信念、生活模式、价值趋向,如同从幕侧伴奏的笛声到舞台中央的交响乐。具体来说,对农家而言,读书不再是奢侈品,而成为必需品;对士人而言,耕读不仅是科举必须,也是生活乐事。这一强化与转变,完成于宋代。这与宋代农学大发展、成为北魏以来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正相一致。
耕读统一才能形成耕读文化。耕读文化是文化普及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形态,把文化融进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并与之并列,号召士人像重视读书一样重视农业,号召农民像重视生产一样重视文化。正如两宋之际的李石在眉州劝谕百姓耕读结合时所云:“俾田与孝同力,稼与学并兴。”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举的模式,既是生产模式,也是生活模式,广大士子因而有了实实在在的起点和落脚点,广大农家子弟因而有了文化武装和前途希望,使农业文化有了新发展,使文化与农业较好结合,对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是具有直接且深远的作用。特别要指出的还有,耕读模式增强了阶层之间的对流性和代际流动性,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的代际焦虑,使底层农家子弟有了长期发展愿景的感召力和凝聚力。是为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产物,经宋人的确立宣扬,遂成为优良传统的经典,是农耕文化的升级版,成为中国古代后期一种标准的生活模式,也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更新与完善。其阶层结果,就是造就了明清的乡绅。
但是,平心而论,耕读文化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,从后代的历史情况来看不能评价过高。尤其是在政治上并未产生多大积极影响。耕读文化是一条固定的上下通道,其理想状态是既通天又接地。实际上,从明清时代的流行情况看,上下垂直的动态并没有质量的变化,并不能打通传统文化发展的“任督二脉”。被美化成田园诗的耕读文化顺从并固化了农耕思维,耕读的百姓有了自我修复能力,相应地也顺从并强化了君主专制主义,使之稳稳地落实在农耕大地,如系舟之锚,牢牢固定在大地,专制主义之舟从此只有前后左右的飘荡,中国政治不再航行前进。正如陈尃言:“知夫圣王务农重谷,勤勤在此,于是见善明而用心刚,即志好之,行安之,父教子召,知世守而愈励,不为异端纷更其心,亦管子分四民,群萃而州处之意也。”世守而愈励的耕读文化,目的就是“不为异端纷更其心”,可谓一语道破。故而,耕读文化只能改变个别农民的命运,不能改变群体农民命运。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,直到西学东渐之前再也没有大变化。因为普及的耕读人家主体已经不是以往少数自由自在的隐耕士人,而是农村士绅和农民,从“野生”到“圈养”,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自在,落入世俗的牢笼;况且,经过理学强化的耕读文化贯彻着孔孟之道,不可能滋生新思想新文化。当然,这些反思都是题外话了。
近来李治安先生总结历史,提出了“耕战模式”概念。指出:“自‘商鞅变法’滥觞,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,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。它历经秦西汉的鼎盛、北朝隋唐赖‘均田’‘府兵’及‘租庸调’的再造复兴和明代‘配户当差’为特色的最后‘辉煌’,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表演不同凡响。作为马克思所云‘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’典型体现的编民耕战模式,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,尤以徭役、兵役沉重,故特名‘耕战’。其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。”这一论断甚有识见,但宋代社会与之不同,不在“耕战模式”推行之列。那么,填补这一时代空间的,或许正是“耕读模式”。并且由“耕战模式”的政府行为变为“耕读模式”的个人行为,由政治现象变为文化现象,因而更有生命力。实质与目标,却都是一样的。
作者程民生,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注释从略,完整版请参考原文。
编辑:老 胡
校审:水 寿
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订阅号
历史中国微信订阅号


本文 zblog模板 原创,转载保留链接!网址:https://3720squad.com/post/316.html
1.本站遵循行业规范,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;2.本站的原创文章,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,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我们将追究责任;3.作者投稿可能会经我们编辑修改或补充。